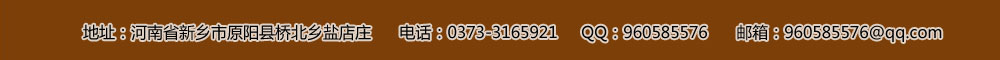宅与渣,信息时代的社会病
“假道学”、“真小人”一锅烩的时代到了
人类起初对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毫无办法,只能膜拜、供奉,在相对于它的“依赖”与“独立”需求相互转化着满足的过程中,与之建立了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这种关系应生到人类群体,领袖与群众、丈夫与妻子,家长与子女……都形成了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群落的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逐级细分,家族的管理与被管理地位逐层细化,渐成体系。
与此同时,人类相对于客观环境中的阳光、空气,尤其饮食对象的“封闭”与“开放”需求相互转化地满足,加剧了人类对大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
与面对大自然不同,人群对于采摘、渔猎的饮食对象,以及其他个人和群体,具有旗鼓相当的主观能动性。饥渴难耐又采摘不到食物的时候,人群会攻击、杀戮其它动物,以及其他人群及个人;也会被对方侵犯、劫掠。
水源通常充足,饥饿随时袭来。它的内驱力,远比人类对适宜的“生存空间”的渴望,发作得更猛烈而频繁。个人只有合群,才能共同捕获食物,抵御豺蛇猛禽走兽,以及他人、敌人侵掠,存活下去。
待到个人及其家庭普遍营造了居所,配备了家居用品,其居所与家居用品也和食物一样,成为可以被其他人劫掠的对象。由此,适宜的“生存空间”,加上饮食、夫妇和炊烟,成为人类最早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族为聚居单位的“生活空间”;再扩大就是聚落、部落形式的,宜活的“生活空间”,以及地域范围内,包含了日月、星辰、阳光、空气的,宜生的“生活空间”。
“生活空间”及其中的具体需求对象(既有和新创造的),即是人与人合作、竞争甚至争夺的对象。个别群体由部落发展为诸侯国、王国,其中相对独立且共生的人群以领地、村落、封邑等形式存在。
在人与人依附且被依附的群体范围内和外,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合作、竞争、争夺持续深化,相应攻击、防御的态势也不断升级,其张力笼罩所有人的身心。而个人相对于他人的“封闭”与“开放”需求满足的形式、心理及其变化,不断超越共事与敌对,升格到智谋和权变。
个人与他人沟通、交流,其“开放需求”的对象是可交换、可共创的“生活空间”,及其中具体的需求对象,具体包括衣、食、住、行及锻炼身体相关的居所、家居用品、器具、设施,以及研发、生产它们的经验、工具(器械、设备)、工艺、配方等。
当这些都可通过货币交换,或资源互换,个人与他人沟通、交流,其“开放需求”的对象即是“货币”、“资源”(二者的合并即“资本”)。如果个人不是为了“等价”交换、合作共赢,而是直接瞄准他人的“生活空间”及其中具体的需求对象,那是盘算巧取豪夺了。
正因为有此种风险存在,所以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沟通、交流,通常不会完全敞开心扉,彼此互有保留,这是双方“封闭需求”的满足形式之一。
在彼此的“生活空间”相对适宜、互无侵犯的条件下,个人相对于他人的“开放”与“封闭”需求的满足自由转化。但其中潜藏着不自主的可能,即一方被迫,或被对方牵制,表达了不能说的密秘。这或可成为对方立即发作、延时发作,巧取豪夺其“生活空间”并其中具体需求对象的“武器”。
如果双方的“生活空间”都很恶劣,便须互相堤防;如果一方的“生活空间”很恶劣,另一方的很优越,那后者就更该堤防了。因为理论上看,“需求”具有蛮力,会驱动任何人很冲动地攫取任何需求对象。个人所处的“生活空间”越恶劣,急于改善甚至摆脱之,劫掠他人的冲动越强烈。
在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个人相对于他人的“开放”与“封闭”需求的满足便不自由了。他或者主动出击,暴露实力,倾向完全“开放需求”的满足;或严防死守,全力防御,倾向完全“封闭需求”的满足。
这是个人相对于他人的“开放”与“封闭”需求的满足及两种需求的相互转化,侧重于心理而非身体。落实到作为上,其主要表现形式便是合作、竞争、攻击、防御。另有情况是双方互相请吃、住,其“开放”与“封闭”需求的满足及转化侧重的即是身体,而非心理。
个人相对于他人“开放”与“封闭”,只是社交的一类表现形式,不能等同于社交,因为其需求对象针对的主要是“生活空间”及其中具体需求对象。单纯以休闲、娱乐或者寻安慰、找对象为目的的社交也相当普遍,但个人在其中寻求的是其它更高层级需求的满足,而且涉及人所处的客观环境及条件也不一样。
“生活空间”及其中具体需求对象,是财产、财富中满足个人“依赖”与“独立”、“封闭”与“开放”需求的那部分,不能等同于财产、财富。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方便阐释“封闭”与“开放”需求,把它们与人类其它层级需求及其需求对象区分开来。
如前所述,人类的“依赖”与“独立”、“封闭”与“开放”需求都追求“信息级”无限满足,及“宇宙级”无限扩张。
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一个客观事实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即个别人、少数人越来越精细并膨胀的衣食住行及锻炼提升的需求,必须他人、多数人共同劳动才能满足。同时,个别人、少数人需求满足的“感性体验”与相应需求对象融合得越紧密,越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向他人、多数人索取更多。
在依附与被依附的人际关系普遍形成的客观条件下,“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分日益明显。两者在外表、作为、心理、生活等各个方面差距拉大,鸿沟深隔,以至于前者不把后者视为同类,厌憎之如蝇臭,驱使之似牛马,杀戮之如弃履。
长期不劳而获(成长阶段乃至以后)加上需求无条件满足,令人沉溺在需求满足的“感性体验”里,其“理性意识”被牵曳着围绕适宜的“生活空间”及其中具体需求对象层层“编码”,完全体味不到他人的疾苦与艰辛,个别人、少数人因此整体趋向自私、狭隘而贪婪。
偏偏他们又物质条件得天独厚,精明算计自幼培养。于是,阶级、阶层一再分化,统治者针对被统治者的整体剥削并掠夺、欺压加凌虐,成为必然。
导师恩格斯写道:“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而人类的“依赖”与“独立”、“封闭”与“开放”,再加上尚未论述的“性爱”与“传承”需求,即是导师指责的“贪欲和权欲”的人性基础。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自然法则尊重人类的整体进化,不会任由自私、狭隘而贪婪的人长久。他们施加给社会的重担,必然促使其他人奋争。
而且,随着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积聚,越来越多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挑着“重担”前行,赢得其更高层级心理需求的满足,又必然促进社会思想文化及艺术的繁荣——人类需求的整体满足及整体素质,由此具备了螺旋上升的可能。这一螺旋上升的趋向,恰恰包含了自私、狭隘及贪婪的反面。
人与人之间依附与被依附的上下阶层关系,被圣人简洁地概况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同阶层的人之间,也须禁止相互攻击,加强合作与和谐,才对群体最有益。所以圣人宣扬仁爱、互义、守信,并强调个人的行事作为合乎公道,由“智”明辩是非,羞私恶(wù)恶(è)——它们一起成为制定“礼仪”的准则,共同成为国家级的伦理规范。
其它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的主张很多,大抵围绕人的需求满足及克制提出。比如老子主张天人和谐、小国寡民,无欲无求地过小日子。墨家除了力行与人为善之外,倾向“独立需求”的满足,过苦日子。法家倡导用严刑峻法规范人的需求满足,并且明确了个人与国家进行“价值(利益)交换”的准则,有功则赏,犯过则罚……
不过,在依附与被依附的人际关系既成事实的客观条件下,所有圣人都刻意回避“平等的价值(利益)交换”这一概念,并从未寻求“个人社会价值标准”的制定与推广。统治者更着重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拎出来大肆宣扬,同时把赤裸裸逐利的商人排在士绅、农民、手工劳动者的后面,仅差一步就沦落到下九流了。
等级社会制度之下,“平等”提也没用,但是“耻谈利益”的洗脑却流毒深远。特定时间段,农民能打多少粮食,手工劳动者能做出多少成品,文艺工作者能创作多少文化出品,商人能流通多少营业额;他们该纳多少粮、缴多少税、留多少余财过日子,不难估算。
相应,当官的、为君的能带领一帮下属,或者一方百姓,创造多少价值,分配多少价值,个人应享用多少价值,也能核算清楚。
但是在“耻谈利益”的氛围下,所有价值和财富煮成一锅粥,混成糊涂账。天子做为“神”的代言,未断奶都能坐在金銮殿上接受百官朝拜、万民景仰、四方来贺;最大量财富自然向他汇聚。
官员披着忠、孝、仁、义的虎皮,拼命搜刮民财。士绅、道学家拿着朝廷的打赏,挂着朝廷的奖章到处忽悠——只有百姓傻乎乎地做牛做马,任凭宰割,暗无天日看不到头;他们还自以为有君子之风,没做小人。
数千年下来,整个伦理体系、宗法制度沦落得“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最大获利者都是那些“做着婊子立牌坊”的假人。到了物极必反的节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才一股脑扯下它的遮羞布,开国元勋们继而在它的废墟上建起了新中国。
或许前面一百年用力过猛,如今“假道学”荡然无存,“真小人”举国认同。当下流行的行为准则是:“人傻,钱多,速来”;“别和我谈感情,谈感情伤钱”——人人都以金钱标准衡量一切;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巍巍然矗立起来。
这样也好,“谈钱”恰符合人类“封闭”与“开放”需求满足的初衷。只是,圣人规范的伦理、法律体系,道德、行为准则中的“真道学”还须光大。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须重新诠释、遵行。
不管什么家境,什么处境,个人相对于他人的“封闭”与“开放”需求的满足都面临三个选择:一是不劳而获,巧取豪夺;二是协作竞争,共同创造新价值、新财富,并按劳分配;三是平等的价值(利益)交换。至于直接攻击性劫掠,自有法律严惩,所以不算在其中。
这是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发展观”的选择。第一选择已经被历史一再否定了,注定长不了;二、三才是当下时代所需。只是,其中关键在于价值(利益)分配及交换的标准是否公正、公平、合情、合理,可否精确量化。
倘若具备了这一前提,人与人之间尽可敞开心扉,充分满足各自相对于他人的“开放需求”,而不必遮掩、躲闪,令人感觉虚情假意、虚与委蛇,其“封闭需求”还在没必要地满足着。
个人如此,他人如是。归根结底,“个人社会价值”决定一生的成就。只是从前“耻谈利益”,把它糊在锅底。现在一旦拎出舒展到阳光下,或许,人类的前景就兜了个轮回,在更上一层螺旋的高点上,悄然绽亮了。
“宅”与“渣”,信息时代的社会病
在“笼子”里待久了,身心会与“笼子”融为一体。较典型的事例是“密室监禁”,受害者竟会对监禁她的迫害者产生爱慕,甚至一起拼命对抗试图解救她的人。被解救后,受害者通常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须他人养护才能存活。
现实社会中,多数人活在比“密室”大不了多少的“笼子”里,逐渐与之融为一体。正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先生把这称为“惰性”。而“惰性”的背后,藏的是立基人性的“需求”。
“依赖”和“独立”需求的满足是“封闭”和“开放”需求满足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它们在生命(单细胞生物)诞生前就已经形成,之后由于后者吸纳吞吐,相对外显,就把前者掩盖了——从生命演化的宏观角度看,它们都是人类先天的本能需求。
仅这两对需求满足,个人就能存活,并逐渐与世隔绝,沦为“人形哺乳动物”。古今中外历史上有诸多极端例子:
王莽篡汉后,把年仅4岁的汉朝太子刘婴软禁,通令禁止任何人与他讲话。待刘婴长大后,六畜不识,话也说不清楚;刚活过二十岁,就稀里糊涂被叛军杀了。
明朝洪武年间,安徽歙县许村有位胡氏,不到二十岁守寡。之后52年,她被养在一个筒子房里“守节”,只留一个洞口供人搭梯子进出送吃喝,直到去世没出去过。现在这地还成了景点,叫做“墙里门”。
年,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见到了著名的“铁面人”,据记录,他已经在牢房里关了三四十年。同样在法国,年,波皮尔市的警察从阁楼单间里救出形如骷髅的布兰奇·蒙尼尔女士,其时她已经被母亲囚禁在里面25年,只因为想嫁给自己心爱的人,拒不屈从于母亲的指婚。
最极端的是汉朝吕后,把情敌戚夫人割鼻、挖眼、封耳、破坏声带、剁掉四肢做成“人彘”,装瓮扔厕所,还召亲儿子孝惠帝观赏。《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孝惠帝看后,惊吓过度,此后“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而戚夫人,由于每日被喂食饮,“人彘”样的还活了一年多。
天性“封闭”的人自然倾向与封闭的“生活空间”及其中的“封闭对象”互动,久之形成“内向型性格”;天性“开放”的人自然倾向尝试或挑战“封闭对象“的新变化、非适宜成分,与开放的“生活空间”并其中的“开放对象”互动,久之形成“外向型性格”。
作为高一级需求,“封闭需求”的满足沿着“依赖需求”满足的方向发生,其需求对象既指熟悉且已验证安全无害的阳光、空气、饮食,也包括适宜“依赖”的居所、家居用品等。
“开放需求”的满足沿着“独立需求”满足的方向发生,其需求对象包括阳光、空气、饮食中令人不适的“成分”,未曾体验的新波长阳光射线、新空气成分、新型饮食,还包括非适宜的“生存空间”及其中满足“独立需求”的具体对象。
“依赖型性格“的人被迫长期与开放的”生活空间“互动,他会小心谨慎地适应其中必要的“开放对象”,将其转化为自认为舒适、安全的“封闭对象”,将自己再次“包裹”起来。若是他一直处身于封闭的“生活空间”,更是如此。
“独立性性格”的人被迫长期处身于封闭的“生活空间”,自会从其中舒适、安全的“封闭对象”不断挖掘出些“新意”。倘若由于个人经验不足,或客观条件不允许,再无“新意”可挖,他会焦躁、厌倦,甚至乖张失措乱规矩,癫狂错漏搞破坏。
这两种性格分别与矛盾的“生活空间”长期互动,形成两类过渡阶段的交叉性格,即“依赖开放型性格”和“独立封闭型性格”。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它们通常还会回归天性的“封闭”和“开放”。
如此“上错花轿嫁错郎”的情境对任何人都是磨练。它发生在个人成长阶段,调控得当,能极大促进个人提升;反之则易夭。它发生在个人成年阶段,外力过小,对他不起作用;外力过大,则把他折断。
战胜天性也许可能,个人得学通“天地人”,自知又知人,而且具有强大意志力、自制力,不滞于物,不拘于己;擅用一切外力与自力,成就社会、追随者及自我。
如果说“依赖”和“独立”需求还驱动人眼、心朝天,夜观星象,探索风霜雨雪、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封闭”和“开放”需求则主要驱动人眼、心朝地,甚至钻地三尺、挖窟窿捣眼地寻找菜根、知了狗、泥鳅、螃蟹……
毕竟,与追求适宜的“生存空间”相比,针对饮食的“封闭”和“开放”需求更强烈,且更频繁驱使人类,而人类的饮食又以陆上、地表的动植物为主;浅水层鱼虾尚可捕获甚丰;指望射鸟裹腹,就太劳力费时饿肚子了。
有房遮风挡雨,为饮食,个人必须“现实实践”,与客观环境中的他人、人工出品、自然物、文化出品打交道,提升“现实实践经验”;并主要从“文化出品”中进一步了学习、掌握谋生用的“唯物教条经验”和“虚拟现实经验”。
基于“依赖”和“独立”需求满足,个人的“封闭”与“开放”需求针对既有及全新的需求对象不断相互转化着满足,他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空间”才能持续提升并拓展。由此,其需求满足的层级自然递增——对于成长阶段的个人来说,少年末段,即萌发“性爱需求”,其“传承需求”也会在随后几年或早或晚发生。
“外向型性格”的人独立、自主。他开朗、乐观,敢想、敢干。对于非适宜的“生活空间”,他勇于尝试、挑战,并努力适应。面对异性,他骨子里放得开,能较快接受一位恋人,品尝禁果;分手之后,也能快些调整心态,开启下一段恋情。
“内向型性格”的人驯从、依附。他保守、内敛,慎思、谨行。别说非适宜的“生活空间”,即使锦衣玉食的豪门爵府,他也不会轻易跨进去,总感觉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最舒适、安全。异性的追求他不会很快接受,处久水到渠成了自然合在一起。从此,他心心念念为两人着想,既会照顾对方也善待自己。
过去,婚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多数年轻人的需求满足递增在“性爱”和“传承”这层就被挡住,或至少没称心尽性。好在人类需求的满足可以同级相互转化:不满意爱人,“性爱需求”的满足不如意,可以把心思转移到子孙身上,在“传承需求”方面寻满足。
转化不得,需求的满足还可以上升、倒退。只是,单一需求的满足直线升级,而不是同级需求相互转化着递增,久之必然养成个人偏执的性格。“倒退”是需求满足受阻寻找替代的自然态势。过去的年轻人倘若婚姻不如意,男人或可三妻四妾、外面风流快活;女性的需求满足,通常奔“封闭”去了。
在信息传播极不发达的前提下,倘再不识字,新婚妻子的信息来源只是家长里短、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如此,她这辈子就只剩下端茶倒水伺候公婆、男人、子女的命了——小户人家的少妇必须忙里忙外,大户人家的少夫人可绣花、遛狗打发时光;她们的身心,被画着“穿衣吃饭”四字符咒的黄布条逐层缠绕,直到裹成“干尸”埋土里,一生满足的,大抵只是“封闭需求”。
男人的“生活空间”比女性大得多,但基本近成年即定型。升官发财、建功立业、叱咤风云、改天换地是少数人的事,绝大多数务农、做工及下九流的男人,其“封闭”和“开放”需求相互转化着满足的具体对象是稳定的他人、稳定的人工产品、稳定的自然物,其“性爱”和“传承”需求满足的具体对象是稳定的女人、逐个增多或夭折的子孙。
他一辈子,大多走不出所在的村县或府市,偶尔出去一趟也只走马观花即回。表面看,他昼劳夜息、养家糊口、走亲访友、养老育后,生活忙碌而充实。但究其本质,他一生追求的,也是自家人“穿衣吃饭”。
虽然他不像女子一样整天围着磨坊、锅台、针线笸箩转,但依然只是在大些的“笼子”里团团转。晚年终日回顾,发现所有能忆起的不过一方水土一片天;除了寄托给子孙的希望,没有任何其它生命亮色与自己的作为关联。
久处在“笼子”里,“笼子”便长在身上。偏偏这“笼子”还背不动、带不走、摘不下,离开些时日便朝思暮想、牵肠挂肚、星月黯淡,感觉再不回去命都没了。
太平盛世不过如此。遭逢天灾人祸、战争频发,男人、女人拖家带口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他们内心天塌地陷、孤苦伶仃、茫然失落的恓惶可想而知。其时但凡有人能让他们过回安稳日子,便是人神、天神、菩萨、佛祖。一代人感恩不够,还得子孙后代五体投地的顶礼膜拜。
这样的饮食男女一茬又一茬繁衍不息,至民国长成了铜头瘴脑、麻木不仁的“看客”。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心、眼朝地,泥土里刨食。其需求的满足,至“性爱”和“传承”层级就被糊住了气息。其人生经验的积累,除了“刨食”的技艺,只有伦理纲常的碎念、神狐鬼怪的传说,和奇闻异事的传言。
当今时代,初中级教育普及,信息爆炸,物质极大丰富,但个人的需求并非大部分顺利满足并自然递增,反而因此更受挫折,远不如前人平淡苟且知足常乐随遇而安。
究其原因,首先是新新人类被开了“天眼”,但封了“天念”。
所谓“天眼”,指“眼界”。上下四方、往来古今、当下时事、万千商品、无穷享受,鼠标点击、手指滑动,图文、视频、3D、全息形式的信息尽皆收入眼底。
前人想象皇家王族的生活,以为他们天天睡火炕吃莜面加肉烤腰子嘬糖,如今金銮殿养心斋上书房满汉全席总统套房米其林三星银河系宇宙全景随时随地可“观”。
所谓“天念”,指神灵鬼怪轮回转世天堂极乐观念。如今新新人类大多认为人死如灯灭逝后无再生,由此滋生了“即时享乐”的紧迫感。这种自然观、生死观成为当下构建人生经验的普遍心理基础。
其次,新新人类是“不劳而获”长大的当代人。他在儿童、少年甚至青年前期性格养成的关键阶段,普遍脱离生产劳动和竞争协作实践,积累的人生经验主要是“唯物教条”和“唯心虚拟”经验。其行为处事在步入社会之后,也习惯以此两类人生经验为指导。
这使得他倾向“借力”满足自己的需求,受挫后则自然归因于他人、外物及社会。而且,与”现实实践“隔膜的“唯物教条”和“唯心虚拟”经验,极易被舒适刺激的“感性体验”和“感性想象”牵着鼻子胡乱指令,其中的万千商品、无穷享受自然排山倒海似的,迷乱、席卷他的身心。
再者,花钱容易赚钱难。即使人到中年,大部分新新人类凭月收入,进不去商场,迈不进酒楼、酒店,更何况还要养家糊口,供子女成家立业。年轻人即使月月精光,也难得出去休闲、娱乐几次;买单且不说,AA也犯难。
另外,社会各阶层,甚至同事之间,个人收入、家境也分级明显,其差距还日益精细地体现在所有衣食住行及休闲、娱乐的用品、用具及场所等具体对象上。
明星站在聚光灯下,尚且被品头论足,动不动由于衣着、首饰、言行不当被身边人“秒杀”。吃瓜的年轻人出门交际,自尊心受挫,其“归属”与“自尊”需求的满足遭俯视、冷眼、窃议式受阻,再平常不过。
如此,“性爱”和“传承”需求满足之上的自然递增差强人意,被迫倒退。而面对气象万千的花花世界及其中万千商品、无穷享受,“依赖”与“独立”、“封闭”与“开放”需求的“信息级”无限满足和“宇宙级”无限扩张动不动遭阉割,普遍困扰新新人类。
庆幸的是,前人“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实际上很难实现,如今“宅”家里观天下风云、览古今中外、赏宇宙气象轻易即得,网购、外卖给了“宅”人不出户自足的便利。当下年轻人早就离不开适宜的“生活空间”,“宅”家里享受“封闭”与“开放”、亦或“性爱”与“传承”需求的满足实属自然。
而且,模拟现实、平添虚幻的“游戏空间”还提供给他另外一种可能,即在“唯心虚拟世界”指挥千军万马、拥揽玉颜美人、挑战鬼怪神佛……这可以令他实现“性爱”与“传承”之上各层级需求的“虚拟满足”。
接下来,“宅”人有三个阶段性的人生方向选择:一是依旧不劳而获,啃老、啃天、啃地,把自己与适宜的“生活空间”和休闲、娱乐的享受对象一层层包裹起来,最终归宿于“封闭需求”的满足,与“笼子”融为一体。
二是利用网络联结人工出品、自然物及文化出品,与他人进行“价值(利益)交换”,实现电子商务的盈利。这样可以逐步把线上交易转为线下交际,实现现实的更高级需求满足,打破“宅”局,回归现实社会。
三是结合时事变幻,不断学习、积累“唯物教条”与“唯心虚拟”经验,创造以“文化出品”为载体的“个人社会价值”,并通过与他人的“价值(利益)交换”赢得回报。其创作除了人所共知的自媒体内容,更包括科研、文学、艺术等出品。
倘若像普鲁斯特,十五年“宅”居,写出《追忆似水年华》;或者像熊谷守一,三十年不出门,因画作被誉为“艺术世界的隐士”——如此,身体自觉包裹,“意识”流溢光华,一生也算“宅”出至高境界了。
很多年轻人不甘心被“宅”,又创造不出可观的“个人社会价值”,赢得丰厚回报,以支撑自己在现实社会衣着光鲜、代步亮丽地进出,实现“性爱”与“传承”之上更高级需求的满足,于是“借力”异性为登高的阶梯,并且像“蚂蟥”一样吸干血即转换目标。这就走向了“宅”的对立面,而且步入了“渣”的行列。
古人对这一作为的主观前因早有形象描绘,即“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由于腹无点墨、身无特长,又出身平庸,这类“新新人”还想不劳多获,才如此存活。
其过程损人利己,其结果令社会整体价值及财富不增反耗。由于对人情、世事、社会、自然规律缺乏理解,就“渣”人的个体生命进步而言,其需求满足缺失“内在考量”与“外部实在”的互通、共融,不会逐级递增,反而自然倒退到衣食住行享受的“封闭需求”满足。
如此,“渣”人尽管费劲巧思、周折,但其人生归宿依然逃不脱把自己层层包裹为“干尸”,先圈进“笼子”,再埋到“笼子”下面的土里。
当下时代,“宅”与“渣”已经成为流行的社会病;其病根深远,其病因错乱,其养成关键在于儿童、少年性格成型阶段的教育,以及青年人生定型阶段的社会引导。只有把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引导的弊端清除了,天下无“笼”的人类进化阶段或可发生。
热点文章

最近更新